群体合作中的必要惩罚
作者:马建红 法学博士
在传统法律文化形成过程中,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儒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提出德主刑辅、礼法并用的主张,强调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要以礼义教化为大务,教化犹如堤防,具有禁奸止邪的功能,古圣明王以教化为急务,才能君临天下,实现大治。不过,让人奇怪的是,汉儒虽然认为强秦之亡,在于专任刑罚一端,但他们的态度,却是在提倡礼乐教化的同时,强调发挥刑罚的作用,认为在治理社会中,刑罚虽然只是辅助性的工具,但却是必不可少的,礼乐教化与政令刑罚二者交相为用,才能实现统治的效能。
有时候,真的很佩服我们祖先的智慧,他们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乏对大同理想的追求,然而这种追求却又是脚踏实地的,注重实效的。比如董仲舒,他没有凌空蹈虚地清谈人性的善恶,一味地迷信道德教化可以在所有人身上发挥作用,可以解决一切问题,而是认为人虽都有为善的本质,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只有通过教化才有可能为善;至于另外一些人,则是难以教化的,对他们的违法行为,只能施以刑罚制裁,才能使之回归正途。
古人在谈及社会治理模式中,对惩罚的不讳言、不矫情,体现的是一种务实的品格。在现代社会中的一些仅仅依靠社会成员的自觉、反对惩罚或无惩罚的实验,则无不以失败而告终。我们可以看看这方面的实例。
在美国学者保罗·罗宾逊与莎拉·罗宾逊的著作《海盗、囚徒与麻风病人——关于正义的十二堂课》中,曾讨论有关“惩罚”的作用的问题。在“‘落城’与乌托邦聚落”一节中,作者介绍的“无惩罚”实验的聚落所面临的困境及其结局,就让人很受启发。
1965年5月,三名初出茅庐的大学生,在科罗拉多州特立尼达郊外买下了六英亩灌木林地,他们憧憬将这里建成一个“所有人都可以为所欲为”的乌托邦聚落,也即后来的“落城”的发源地。该聚落奉行“反对外来的威权、强力及胁迫”的原则,支持“自愿配合、自我约束”的理念,认为任何旨在对个人行为施加集体威慑的做法,如惩罚,都违反了落城所承诺的“个体性不受限制”的哲学信念。他们希望通过运用失望、不悦等个人表达的累加作用,形成社会压力,对那些恣意妄为者予以教育和矫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里没有任何规则,甚至连教化的规则都没有,单纯地希望靠人们的自觉来维持聚落基本的秩序。
生活在落城的成员坚信,未来将会有更大规模的社会组织,发现反惩罚模式的价值,并纷起效尤。然而,就在聚落建成不久,落城就来了一位取名为彼得·“兔”的“居民”。“兔”对聚落的集体活动不感兴趣,不完成聚落分配的日常任务,不与聚落成员分享其所带来的物资,还从毗邻的木材场盗窃物品。不仅如此,“兔”还自己写作发表作品,其内容有对某些聚落成员的名誉进行诋毁,因此遭到当地警方的扣押。聚落要求成员将自身的全部金钱存入公共的银行账户,而“兔”则不仅拒绝将自己的钱交公,而且还用公共账户中的钱去享用牛排大餐。“兔”自己一毛不拔,却从公款中受益的行为,使得许多人不愿意再将钱存入账户,致使公共账户变得日渐枯竭。对于“兔”的种种行为,虽然聚落绝大多数成员不满意,但却无可奈何,因为秉着不惩罚的原则,聚落不能对其加以制裁。在此种情况下,聚落成员之间已无合作的可能,在创始人纷纷弃“城”而去后,该实验也不得不以失败而告终。
正像作者所分析的,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各种分歧或冲突,像“兔”这样的人,可能会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达到个人自私自利的目的。面对这种情况,个人商谈或社会压力这样的“再教育”,并不会点石成金,培养出集体主义的思维方式,只有威慑性质的制裁,只有惩罚,才能产生这种效果。社会舆论与道德规范能对个人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前提是受其影响的人,必须在乎别人对自己的看法,同时将这种看法放在比自身需要更为重要的位阶。然而,每个社会都有类似于“兔”这样的异类,他不听从一般的说教,也不在意舆论的谴责。这种情况下,要想让社群能继续存在下去,就必须通过设定某种基本规则,使群体核心价值得到尊重,违反者受到必要的制裁。“落城”非刑罚实验失败的悲剧,是对这一规则的最好诠释。
这样的试验告诉我们,在一个社会中,要想合作成功,必须建立相应的规范,要求其成员自觉遵守。对于绝大多数成员来说,道德教化就可以发挥作用,人们异样的目光、舆论的谴责、无声的疏离,都会形成一种使人守规矩的压力。从生存的角度而言,人只有能“群”,才可以保存自我,而要使“群”得以维续,则必须辅之以公平且正当的惩罚机制。由此观之,“德主刑辅”也可以说具有普世的价值。(马建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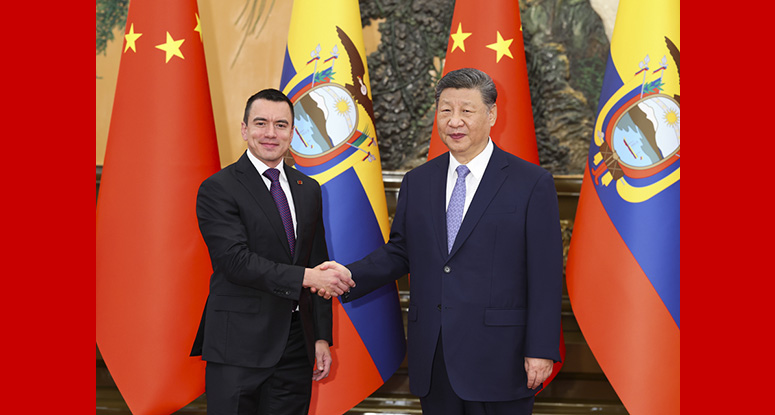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