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伦理学视角看记忆和遗忘
斯温·贝内克/文 郁锋/译
人们忘记承诺、忘记结婚纪念日或亲朋的生日常常会受到责备,而将这些铭记于心则会备受称赞。尽管人们通常认为记得是值得称赞的,遗忘是要受到指责的,有时也恰恰相反。例如,若我只记得他人对我造成的伤害,却不记得我曾对他人造成的伤害,就可能导致我对他人的行为变本加厉。那么,这里的记忆在一定程度上是应该受到责备的,因为记忆在不公正地反映事态。若我忘记了那些曾侵犯我的罪过,而记得这些反而会更伤害我和他人,那么这里的忘记似乎就是值得肯定的。虽然记忆和遗忘通常是道德评价的对象,但令人惊讶的是,记忆和遗忘在伦理学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探究。
我们习惯将赞扬和指责与记住和遗忘相对应,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做法就是适切或正当的。有关记忆的伦理学考察了将赞扬和指责对应于记住和遗忘的做法。在本文中,我将介绍有关记忆和遗忘伦理学中的六个问题,并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1.道德责任的本质;2.记忆和遗忘的道德责任;3.集体记忆和遗忘的伦理问题;4.记忆修改的伦理问题;5.忘记对与错之间的区别; 6.失忆症和对其惩罚的辩护。
道德责任的本质
道德责任理论对主体关于某项行为作出赞美或指责的条件给出了特定的解释。指责由一系列情感反应组成。当我们对某人感到不满或因为某事对其感到愤慨时,会责备他做错了事;当我们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内疚时,也会对自己这样做感到自责。当某人因完成某项行动产生负面情绪反应且这类反应恰当或合理时,他就应为做此事担责。关于遗忘的归责性存在两种解释理论:追踪解释和归因主义解释。
根据追踪解释理论,只要错误行为可以因果地追溯到主体较早的选择或行动并且主体此前是控制了那些选择或行动时,即使行为主体在当时无法控制其错误行为,也应在道义上担责。遵循史密斯(Holly M. Smith)的经典术语,我们可以这样说,对出于无知的不当行为的追踪解释涉及两种行为的序列:一种无知的行为和一种随后发生的无意的不当行为。无知行为是指“行为主体在其中无法改善(或主动损害)其认知状况的行为”,并因此随后完成了无意的不当行为。追踪解释理论说明当一个人在行动发生时,即使缺乏某种对道德责任至关重要的控制或知识时,如何对这项行为负责。在这类情况下,对责任的主张可以通过将主体缺乏控制和知识追溯到其能力未受损时作出的决定上得到证实。按照追踪解释理论,如果我们应对自己的无知或无意担责,则也应对出于无知和无意的行为负责。
追踪解释理论是一种强有力的解释策略,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即使不当行为的主体不知道做错了什么以及在行动之时无法控制自己的行为,也有理由主张应追究他们的道德责任。但是,认为追踪解释理论能够解释所有应当归责的遗忘案例也是令人怀疑的。显然,在一些不当行为的案例中,即使不当行为无法追溯到构成当下道德责任的既往的行为或疏忽时,行动主体直觉上也应担责。例如,塔尔伯特(Matthew Talbert)认为,“至少有可能一些失忆或无意识的行为主体即使之前并没有作恶但也应该为相应行动担责”。
鉴于存在一些有害的遗忘案例,其中在主体无意间做出不当行为之前,没有充分的理由质疑他们记忆的可靠性,因而我们需要寻找不同的道德责任解释。在不当行为无法追溯到无知行为的情况下,我们应如何解释有害遗忘的责任?我们需要抛弃自主性和控制性的条件,并考虑其他替代道德责任意志论解释的可能理论。
归因主义的观点认为,主体因其行为受到恰当的指责或称赞不需要满足控制和意识条件。按照归因主义,主张一个主体因其不当行为而应受到责备所必需的条件只是将这一行为归因于该主体及其对他人的态度。如果一个行为是主体的情绪反应、自发态度和价值观的表现,那么就可以归因于该主体。尽管情绪反应和态度是非自愿的,但也可以使我们洞察到主体的道德人格。有时,这些反应和态度所呈现的情景甚至比主体的自愿行为所呈现的情景更清晰,后者反而可能由于某些策略性原因而掩盖了真实的情感。
根据归因主义,如果记忆消逝表现了行动主体对他人的态度,那么就应受到归责。例如,如果行动主体既不承认自己的过错,且在得知自己的记忆消逝后仍未表现出歉意,则该行为就可以反映出主体对他人的态度。由于主体没有感受到道歉的必要性,他们就会无视其行为影响他人的方式。
毫无疑问,在上述案例中,归因主义的解释策略是有道理的。但是,在某些情况下,有害的遗忘也会使主体对他人的态度毫无意义。为什么我们必须假设不当行为总是反映主体的道德品格?令人担忧的是,归因主义对遗忘的归责性解释,可能会使我们仅为了能够归咎于主体所做的不当行为而误解了他们的道德品格。对此,我提出了一种综合立场,即某些有害遗忘适用追踪理论进行解释,而另一些有害遗忘则适用归因主义进行解释。
记忆和遗忘的道德责任
尽管许多哲学家已经对记忆和遗忘的责任与义务著书立说,但是并没有人试图去表述一种普遍性规则。该普遍性规则需明确,我们应该做到和避免哪些与道德相关的记忆行为,以及如何使人们对此类记忆行为负责。
表面上看来,记住或遗忘,无论是直接造成伤害还是通过不良的道德决策间接造成伤害,都应受到指责。总的来说,(无论是否有外部工具的协助)我们应记住那些对他人而言可能会因我们的遗忘而受到伤害的事件和时刻;我们应在决定是否和如何去行动的时候将此牢记于心。上述规则的例外情况是,我们为了伤害他人而故意建构或存储某些虚构的记忆。显然我们应记忆准确而非错误。毋庸置疑,如何恰当地判断哪些因素对那些可能受到伤害的人重要,以及哪些事情应受到认真对待可能会引起争议。
有时,问题出在忘记了什么而非记住了什么。有意地重述过去的痛苦及抑制可能导致同理心的证据,将会歪曲过去,从而可能导致有害的决策。因此,我们不应以耿耿于怀的方式来重述过去的伤痛,而应建构更加平和、伤害较轻的记忆。这个规则的困难在于,在某些情况下,人们不应始终怀恨在心,同时也不应“宽恕和忘却”。痛苦的回忆也可能帮助我们学会很多。
人们能够从过去的不当行为中学习,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忘记自己的过错会导致道德上的自大(对道德价值的错误表征),并且无法减轻过去的不当行为带来的后果。因此,重要的是,人们要记住自己过去的错误行为,以免造成更进一步的伤害。而且,如果一个人知道自己的记忆力衰退将会导致在进行道德上令人满意的记忆行为时遇到严重困难,那么应该避免将自己置于可能引发危害的境地,或者采取外在的措施来弥补自己的记忆力衰退。
集体记忆与集体遗忘的伦理学
集体记忆的概念是由社会学家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在20世纪初提出的。哈布瓦赫声称,个体记忆的存在依赖于社会群体,甚至在独自回忆的情况下,人们也是从社会的视角或出于社会目的进行回想。在集体记忆中存在着多种现象的聚合,这些现象的特征涵盖了从集合性记忆到集体性记忆的连续过程。集合性记忆是群体成员个体记忆的聚合或共享。相比而言,集体性记忆具有群体、文化或社会的属性,不能还原为群体成员的个体记忆。一个群体内即使没有成员具有相应的个体记忆,也可以集体地记住某些内容。
尽管关于集体记忆伦理学的文献日益增多,但人们对于个体行动者在集体记忆形成中道德角色的普遍化规则仍一无所知。这样的规则是什么样的?集体记忆表明一个社会的重要关切,因此,关于要记住什么以及如何记住的集体决策,要明确注意须在减轻旧的危害和避免新的危害的前提下进行。在建构集体记忆时,我们应努力包纳那些可能因记忆不完整而遭受伤害的人,他们理应被视为集体中的合法成员,并应当注意,我们的建构不会造成选择性的大众失忆。最后,是两个重要的限制条件:我们不应参与形成或维持集体怨恨的集体记忆机制;此外,当集体中的其他人试图使用集体记忆机制造成伤害时,应尽力阻止他们。
记忆修改的伦理学
许多人都希望能拥有更美好的记忆。有些人希望停止或减少记忆的丢失,有些人则希望他们能消除某些痛苦的记忆。除了“低技术”手段(睡眠、运动、心理治疗等)可以改善记忆或减少痛苦记忆之外,越来越多的“高科技”手段承诺能以更精准的方式操控记忆。比如,利他林和莫达非尼等兴奋剂可强化对记忆的巩固,深度脑刺激也可以实现记忆增强。同时,东莨菪碱、苯二氮卓类药物和激酶抑制剂等药物已被发现会阻碍记忆巩固。最后,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新记忆和错误记忆都是可以被诱发的。
记忆修改技术引发了许多伦理问题。记忆修改技术可能会通过拒绝接近某些重要的真相而导致对自身的伤害,使我们失去真正的自我,影响我们的道德反应,减少我们的自我知识,阻止我们履行对自己和他人的义务,增加并不存在的道德责任。此外,一些科技伦理中的常见问题,在记忆修改技术中同样存在。
忘记对与错之间的区别
根据赖尔(Gilbert Ryle)的观点,虽然非道德知识至少在原则上会由于遗忘而丢失,但也有人坦言这是荒谬的:“我以前知道对与错两者之间的区别,但我已经忘记了。”然而,为什么这样的言语行为是荒谬的?赖尔的困惑引起了一个普遍的问题,即免责道德上的无知是否可以得到辩解?对非道德事实的无知(事实上的无知),显然可以免责。但道德上的无知是否也会如此?
关于这一问题,普遍的看法是,免责有关对与错的无知是可以得到辩解的。而批评者则认为,道德无知不能成为一个充分的辩解理由,因为其本身是要归责的。我认为,当前有关道德无知的归责性的争论往往缺乏对人们忘记对与错之间区别的过程的恰当理解。当认真考虑人们忘记正确的道德理论或获得歪曲的道德理论的过程时,很明显,当前关于道德无知的争论预设了错误的前提,即辩解理由能为免责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找到辩解的理由就意味着免责。然而,辩解理由并不是本质上有无的,而是分程度的:可以较弱或是较强,可以或多或少地减轻责任。我将深入探讨辩解理由的强度,减轻责任以及辩解理由、遗忘和道德责任之间的关系等基本概念。我的基本想法为当前文献中两种不同的立场开辟了原则上的中间道路。道德上的无知或许能成为免责的辩解理由,但并不能成为开脱罪责的理由。
失忆症和对其惩罚的辩护
有些刑事罪犯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宣称失忆。这提出了一个令人惊诧却未充分研究的问题,即如果罪犯真的没有了对犯罪行为的记忆,那么刑事惩罚是否是有问题的。根据功利主义的观点,后果的效用为辩护惩罚的正当性提供了理由。在功利主义的语境中,标准的效用是对罪犯的震慑力,对受害人的赔偿,剥夺罪犯的行为能力,对罪犯的改造和救助。因此,从功利主义的角度来看,不管罪犯是否记得自己的罪行,惩罚他们的政策都是可以得到合理辩护的。
如果我们想澄清上述直觉,即惩罚那些不记得自己罪行的人是有问题的,那么与功利主义相比,惩罚主义是一种更好的进路。按照惩罚主义,惩罚的目标是使罪犯感到内疚或自责而悔过自新。如果在犯罪行为发生前后,罪犯没有对行为本身及自身心理活动的记忆,那么他们就没有悔改的可能。如果没有悔改的可能,那么就没有惩罚的理由。这类论证存在的一个问题,也适用于心理上从不会感到内疚和自责的精神病患者。但是,我们反对惩罚失忆症患者的直觉并不会转移到惩罚精神病患者的案例中。
在我看来,惩罚主义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没有找到失忆症患者没有悔改可能的真正原因。惩罚失忆症患者之所以有问题,不是因为失忆症患者无法恰当地感到内疚和自责,而是因为他们无法充分理解这种痛苦背后的原因。对自己痛苦原因的不理解,是一种超越原始痛苦的更大伤害。促使人们认为惩罚失忆症患者是有问题的直觉是这样一种信念,即立法机构不应将不理解的痛苦强加给罪犯。至此,结束我关于记忆和遗忘伦理学六个问题的讨论。
(作者单位:德国科隆大学、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译者单位: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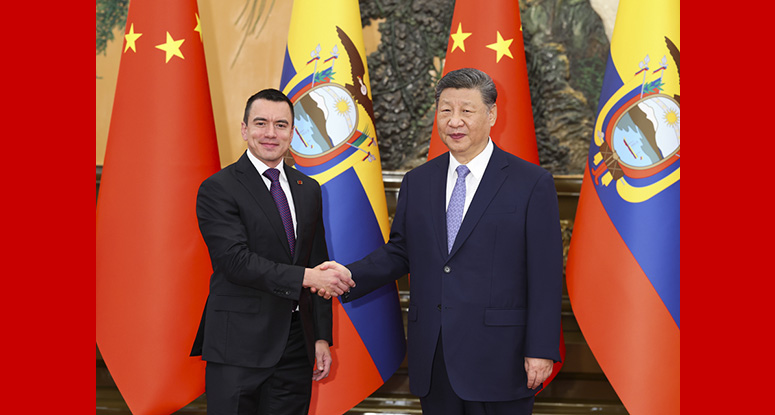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