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理念革新与制度重构
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使野生动物保护问题再次受到全社会关注。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表决通过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为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廓清了方向、奠定了基调。可以说,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既承载了全民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集体反思,也是经由法律变革推进社会变革的重要契机。
立法理念的革新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自1988年颁布以来,经历了2004年、2009年、2016年和2018年四次修改。其中,2016年是大幅度修改,其余3次均为细节性调整。1988年野生动物保护法的立法特色是将野生动物视为经济资源,“以保护促利用”与“利用和保护并举”的立法理念占据主导地位。2016年修改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确立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全新立法目的,但具体制度设计却依然偏重许可监管之下的经济性利用。例如,第1条有关立法目的的表述虽剔除了“合理利用”的滞后观念,但总则中却还有“规范利用”的表述。在具体修改的条文中,对野生动物保护发挥核心作用的禁止性规范,也主要适用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从法律实施效果看,野味市场屡禁不绝,非法贸易常打常存,野生动物产业规模不断扩张的局面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野生动物既有经济价值,也有生态价值,两者如何取舍?从人与自然的关系看,人类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和对生态环境的持续性破坏,已严重威胁到自身生命健康和可持续发展。尤其是在野生动物加速灭绝背景下,如果不能严格控制对野生动物的经济性开发利用,必然对人类造成反噬后果。从国家生态环境治理理念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生态文明”被写入宪法,这为国家环境资源法的发展革新指明了方向。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法应将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立法目的,着力避免将与生态保护目的存在冲突或并非核心任务的立法目的纳入其中。因为诸多法律实践已经证明,立法目的越多元,越容易导致法律实施无法聚焦和精确发力。为此,需要在总则中剔除“规范利用”的表述,增设野生动物全面保护原则、分级分类保护原则以及社会共治原则。至于野生动物的经济性利用问题,则可以在具体条文中作出严格的限制性规定。
制度框架的重构
为确保野生动物保护法真正回归保护法的功能定位,在修法中应准确把握以下核心问题,以实现立法目的与立法内容的完整统一。
第一,明确野生动物分类分级标准,科学制定野生动物保护名录。
对野生动物进行重新定义。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限定为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和“三有”动物,保护范围过于狭窄。一般而言,动物可分为三类: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和家畜家禽。在立法中如何定义野生动物,争论焦点集中在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是否属于野生动物。客观而言,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有的仍长期保持野生属性,有的则显现出家畜家禽的特征。但需要注意的是,在人工繁育野生动物未被依法纳入家畜家禽类之前,不能因为人类对其进行猎捕、繁育和饲养,就否定其作为野生动物的属性。毕竟,公益性野生动物人工繁育目的,本来就是为了促进野外种群恢复。而且,《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易公约》附录一和附录二中的野生动物,无论经过人工繁育多少子代,均属于野生动物。另外,从治理野生动物产业乱象的现实需求出发,也必须加强对人工繁育野生动物的法律保护。因此,野生动物保护法所保护的野生动物,理应包括野外生存的野生动物和人工繁育的野生动物。
重新设计野生动物分类分级保护机制。可以将野生动物分为保育类、一般类和经济类三种类型。保育类是指珍贵、濒危需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一般类是指保育类之外的野生动物;经济类是指允许繁育饲养和开发利用的野生动物。针对三种类型的野生动物,野生动物保护法可以采用差异化的保护标准、保护手段和轻重不同的法律责任。
根据新的分类分级方法,对应建构野生动物保护名录。基于分级保护立场,可以相应制定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一般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以及特种繁育野生动物名录。需要注意的是,在野生动物保护法将引导野生动物产业逐步退出市场的特殊背景下,纳入特种繁育动物名录的野生动物种类应当压缩至必要和最小限度范围内。为此,需要目录制定者综合分析公共卫生安全、科研、药用、展示等社会需求,还要考量政府监管能力和社会稳定等因素,在充分调研基础上,科学制定目录,稳妥回应社会需求。
第二,强化公众的保护义务规定和野生动物的福利规定。
从“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价值理念出发,野生动物保护法的制度设计应当摒弃人类中心主义陈旧观念,注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
强化公众对野生动物的限制性禁止性义务。即强调公众不得对野生动物施加侵害,主要以“禁令—罚则”的形式呈现。例如,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了禁止违法猎捕、禁止违法交易、禁止人为干扰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等。本次修法可以进一步扩大禁令的适用领域,增加全面禁止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动物的规定,严格防范公众对野生动物实施各种可能的侵害行为。
完善公众对野生动物的积极作为义务。例如,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规定了对野生动物的应急救助义务和抢救性保护义务等。修法还应增加防止外来物种入侵、野生动物救护设施建设等义务性规定。与公众的保护义务相对应,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26条规定的“不得虐待野生动物”体现了立法理念的进步,但仍属于最低层次的动物福利。应当说,为野生动物创造安宁的生存环境和条件,实质上也是对人类自身生命健康安全的间接保护。
健全野生动物致人损害的救济机制。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第19条规定了野生动物致害的政府补偿机制。除此之外,关于受害者的自我保护方式、限量捕猎的合法性要件以及建立切实可行的生态补偿机制等问题,也需要立法者予以充分关注。
第三,遵循社会共治原则,扩大野生动物的保护主体,充实野生动物的保护手段。
各级政府应在野生动物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中发挥主导作用,同时,还要发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环境保护组织以及广大社会公众的力量。为此,需要在法律上进一步明确不同社会主体的法律地位、参与方式和行为界限等。为确保社会共治的实效性,应当建立野生动物保护的信息公开和信息共享机制、对协助执法的组织和人员的表彰和奖励机制以及野生动物保护的国际合作机制等。另外值得关注的是,2020年1月27日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通知,要求各级检察机关积极稳妥探索拓展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应当说,检察机关提起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不仅于法有据,而且更加具有权威性和震慑力,也有助于野生动物保护法从政府管理法向社会治理法的改革转型。
(作者:鲁鹏宇,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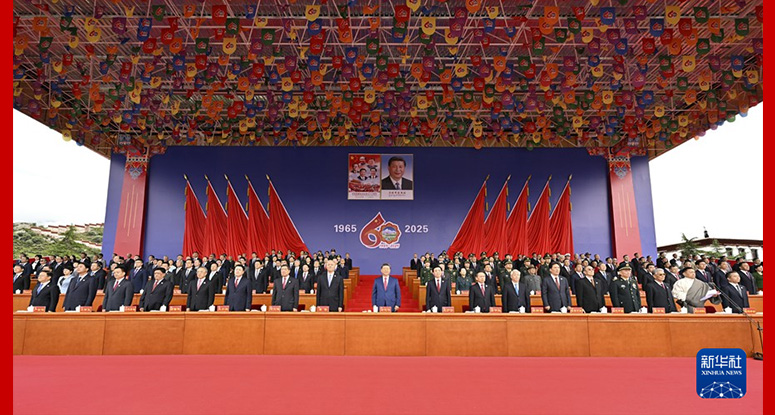



请您文明上网,理性发言并遵守相关规定